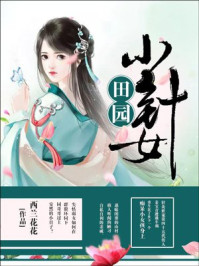芭蕉小说>北地枭首完整剧情 > 第78章 夜宴与抉择(第3页)
第78章 夜宴与抉择(第3页)
只是那赌坊名字荒唐:“野鸡坊”、“烤鸭馆”……输钱数额仅以“甚多”概括,担保人竟还写着“王槐”。
韩齐不是傻子,自然明白其中蹊跷。
他翻动纸卷,心思电转:前几日刘家人还来补办田产地契,说遭火焚毁,怎会全数在此?
这其中的弯弯绕绕,他再清楚不过。
“秦将军,”他神色转为肃然,斟酌着用词,“旬日前,刘家遭火,诸多契据焚毁,这些……”
“那是他们胡说!”秦猛冷笑打断,目光如刀,“明明输给了我,不甘心,便放把火烧宅搪塞。
说不准刘德才、刘耀宗也是金蝉脱壳,假死遁逃!”
韩齐眼皮一跳,牙根暗暗发酸。
本县城巡检司,县衙多方勘验,人,却是死了。
这秦猛看似粗豪,实则词锋如刀,狠辣至极!
他不由得重新审视眼前这位年轻的知寨官。深吸一口气,稳住心神:“韩某还听闻,将军半月前似乎……”
“是,我那时神智昏聩。”秦猛坦然接话,毫不避讳,“但按律:我输钱不作数,别人输我却必须认!连个痴傻之人都玩不过,还有脸赖账?”
韩齐被噎得无言以对,只得苦笑。
这话虽属强词夺理,却在法理上站得住脚,让他一时不知如何反驳。
半晌,他才叹道:“秦兄此举,便是与刘判官不死不休了。”
语气中带着几分提醒,几分试探。
“我知道。”秦猛笑容骤冷,眼中寒光乍现,“他断我粮道、封我漕运,公然针对边寨叫板边军——我若不办他,日后阿猫阿狗都能踩我一脸!”
“可这……”韩齐眉头紧锁,仍在犹豫。
他明白秦猛是来报复的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盏边缘。
秦猛自怀中取出两张银票,面额千两,推至对方眼前。
银票在烛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,显得格外诱人。
“秦兄,这不是钱的事!”韩齐瞥了眼银票数额,心跳慢了半拍,却仍强绷着脸,语气坚决。
“若如此,便是彻底得罪刘判官,乃至整个幽州官场……韩某相帮,便是对立,今后寸步难行。”
这话说得恳切,却也透露出几分真实处境。